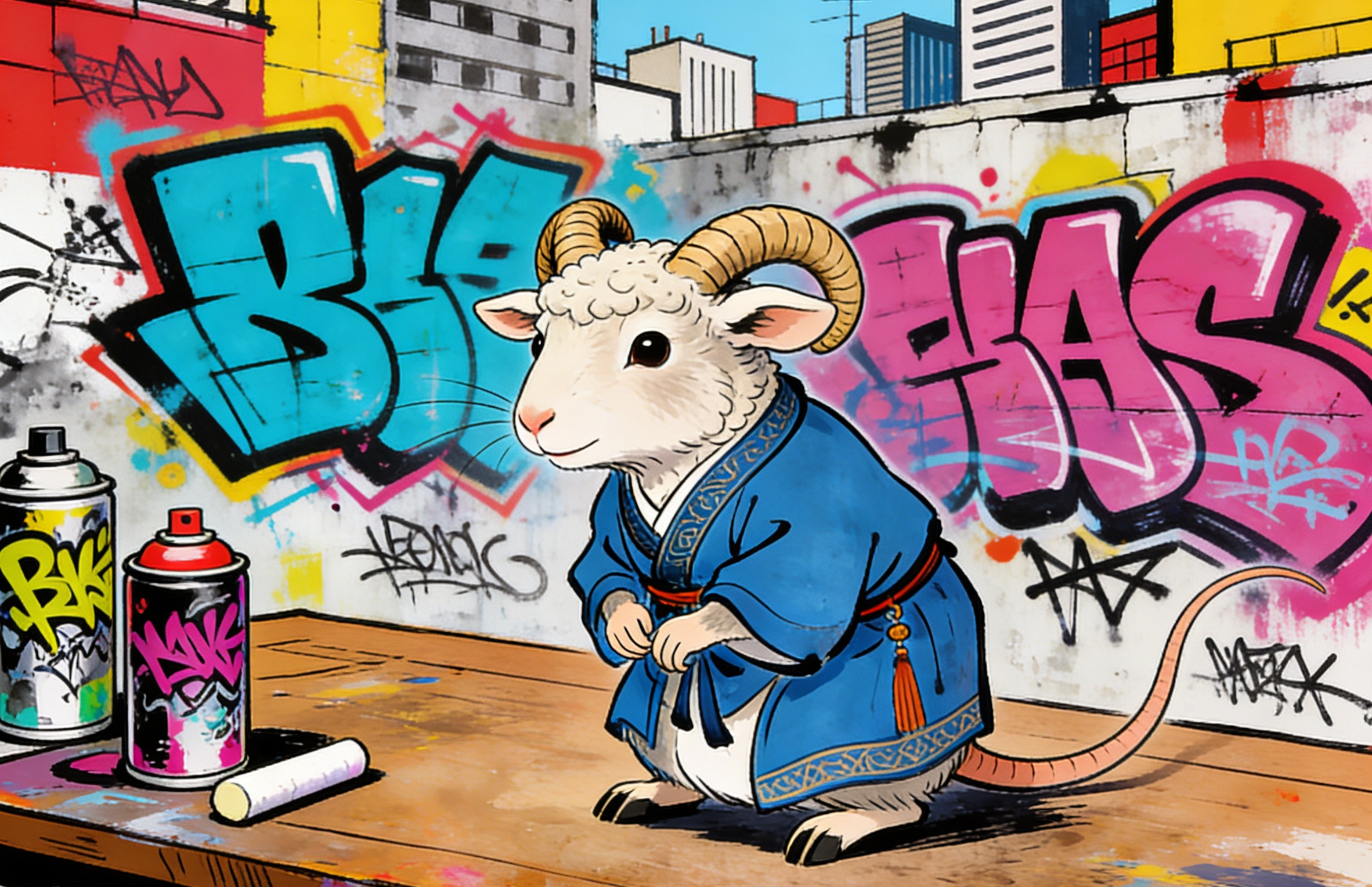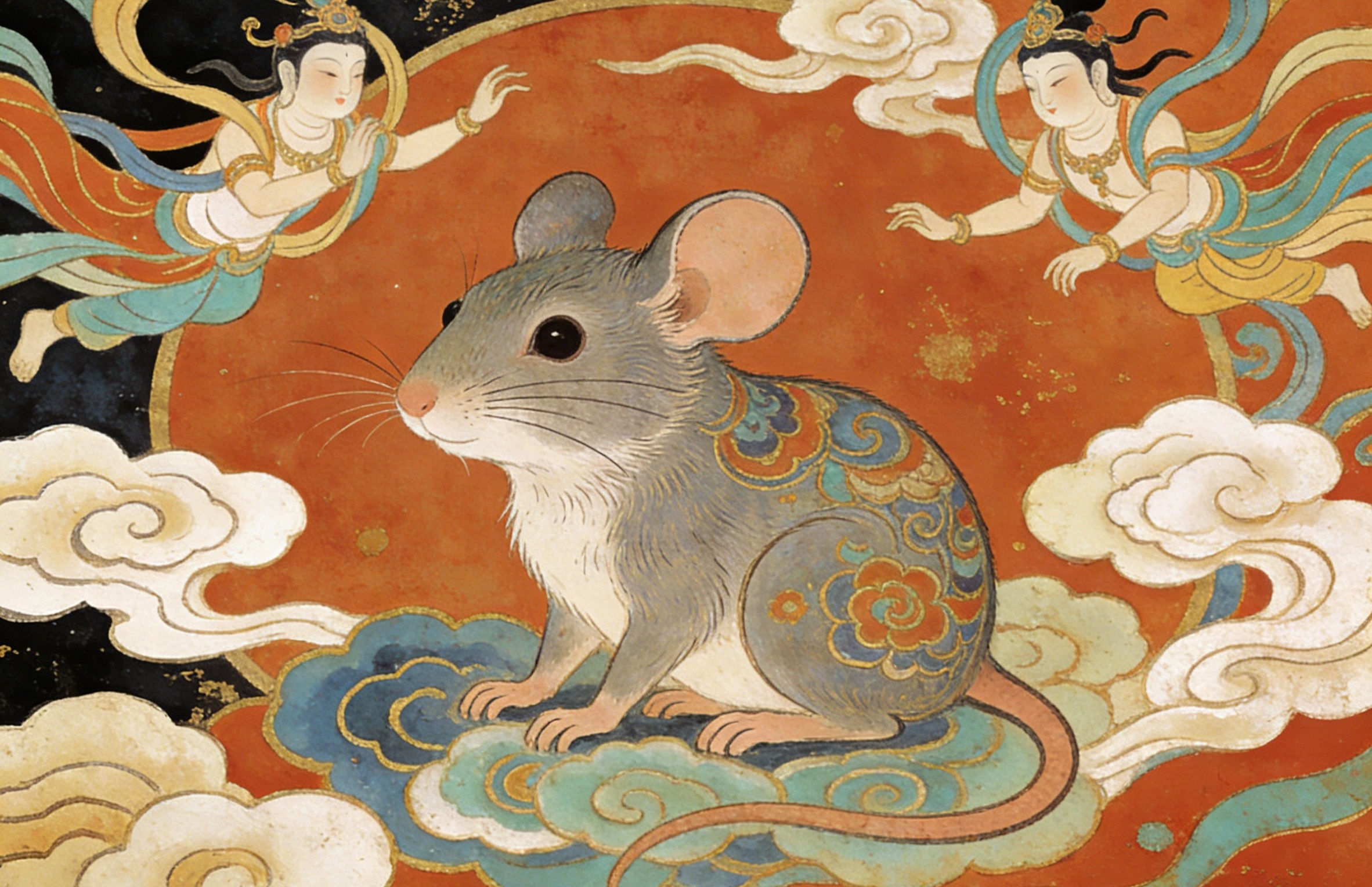老谋深算准确打一个生肖

南京城的烟呛得人嗓子发疼,一种烧焦了的丝绸和木头的味道,混着血腥气。
朱棣成了这座城的新主子,他在一堆瓦砾里,找到了他那个跌倒在地的嫂子,建文帝的亲娘吕氏。
他伸手去扶,像许多年前在老家时,扶起一个不小心踩滑了的亲戚。
他叹了口气,说,大嫂,这事儿我真是没办法。
可吕氏被扶起来后,凑到他耳边,用一种冰凉的声音说了句话。
就是这句话,让这个刚刚得到天下的男人,后半辈子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...
01
天要下雨。
云层黑压压地堆在南京城上头,像一块浸了水的脏棉絮。城外的燕军大营里,一股子烂泥和马粪混杂的潮气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朱棣站在帅帐的帘子后面,只掀开一道缝,往外瞅。
他身上那套打了三年的铁甲,缝隙里都塞满了干掉的泥和血,闻着有股铁锈味。
他一夜没合眼,眼珠子熬得通红,就那么死死地盯着远处那道灰蒙蒙的城墙。
南京。他小时候管这儿叫家。
那时候天总是蓝的,他跟着大哥朱标能从东华门一路疯跑到西华门,跑累了就躺在宫墙根的草地上看蚂蚁搬家。大哥会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,里面是刚出炉的桂花糕,甜得发腻。
现在,那座城像个坟包。
道衍和尚的脚步声很轻,像猫。他走到朱棣身后,身上没有香火味,只有一股子阴凉的霉味,像是从地窖里刚爬出来。
王爷,时辰快到了。他的声音平得像一张纸。
朱棣没动,也没出声。
李景隆那边已经递了话过来,金川门。他的人会把门闩抽掉。咱们的人一到,门就开。道衍捻着手里的佛珠,珠子是黑檀的,被他摩挲得油光发亮。
他要什么?朱棣终于开口,嗓子干得像砂纸。
他什么都不要。他要活命。
朱棣从鼻子里哼了一声,听着像是在笑,又像是在哭。真是大哥的好臣子。
道... 道衍顿了顿,佛珠停了一下。王爷,宫里头的事,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刀剑无眼,但宗室的人,能保则保。
朱棣这才慢慢转过身。他看着道衍那张没有表情的脸,觉得这和尚比他自己还像个做皇帝的料,心里从来不起波澜。我那个侄儿,朱允炆,你觉得他会怎么选?
天子有天子自己的体面。道衍垂下眼皮。
朱棣没再问。他心里清楚,他一路打到这里,旗号是清君侧,是来帮侄儿皇帝扫除奸佞的。
这出戏,得唱得漂漂亮亮。他不能是个提刀的强盗,他得是个心急如焚、来救驾的忠心叔叔。
风大了,吹得帐篷的边角啪啪作响。朱棣觉得有点冷。
他走到案前,从一个旧木盒里拿出一块小小的玉佩。
玉佩是块普通的和田玉,雕了只小老虎,已经被人摸得温润。
这是他十岁那年,大哥朱标送他的。大哥说他生肖属虎,性子也像虎,将来必定是镇守一方的猛将。
他握着那块玉,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些。猛将?他现在是要吞掉整个天下的饿虎。
他把玉佩塞回怀里,贴着胸口。
然后他大步走出帐篷,对着外面黑压压的军队,拔出了腰间的长剑。剑身在黎明前最后一点黑暗里,闪着一道白光。
进城!
金川门开得悄无声息。
厚重的城门像一头沉默巨兽的嘴,缓缓张开。没有厮杀,没有呐喊。
守门的几个兵士,已经被李景隆的心腹解决了,尸体被拖进了旁边的门洞里。
燕军的先头部队像一群幽灵,贴着墙根溜了进去。
然后,城里某处突然响起了一声梆子响,接着是第二声,第三声。这是约好的信号。
杀——!
压抑了许久的喊杀声,如同山洪暴发,瞬间吞没了南京城的宁静。无数的燕军士兵红着眼睛,挥舞着兵器,从洞开的城门涌了进去。
朱棣骑在一匹黑色的战马上,被亲兵簇拥在中间。他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上,感觉一切都那么陌生。
两边的店铺门窗洞开,里面的东西被抢掠一空。
一个绸缎庄的门口,几匹上好的湖州丝绸被拖到街上,沾满了泥水和血,被人来来回回地踩。
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堆书,从一个小巷子里冲出来,嘴里喊着什么斯文扫地,被一个抢红了眼的燕军士兵一脚踹倒,手里的书散了一地。士兵们哄笑着从那些书上踩过去。
朱棣皱了皱眉,但没说话。兵进了城,就是狼进了圈,管不住的。
抵抗很零星,但很顽强。一些穿着儒生衣服的年轻人,拿着刀剑,甚至是木棍,从巷子里冲出来,高喊着保卫陛下,然后很快就被淹没在燕军的铁蹄之下。
血,到处都是血。血顺着街边的排水沟流淌,把浑浊的积水染成了暗红色。
朱棣的马蹄踩过一个被砸烂的拨浪鼓。他低头看了一眼,那拨浪鼓上画着一张笑脸,现在裂开了,像在哭。
越靠近皇城,抵抗就越激烈。
羽林卫的士兵都是勋贵子弟,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,但到了这份上,倒也豁出去了。他们占据了皇城前的牌楼和箭楼,不断地放箭。
箭矢像雨点一样落下来。朱棣身边的一个亲兵闷哼了一声,从马上摔了下去,脖子上插着一根羽箭,血像泉水一样往外冒。
朱棣的脸彻底冷了下来。他看着皇城那高大的红色宫墙,心里那点仅存的怀旧情绪,被彻底磨没了。
给我轰开它!他用剑鞘一指,挡我者,死!
亲兵们架起了小型投石机和床弩,对着那些箭楼开始猛攻。石头和巨弩砸在木制的箭楼上,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。很快,箭楼塌了,守卫的羽林卫士兵惨叫着摔下来。
五家打一个生肖
皇城的大门,在撞木的反复撞击下,轰然倒塌。
就在这时,所有人都停了一下。
他们看到,皇宫深处,奉天殿的方向,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黑烟,像一条恶龙一样,直冲云霄。紧接着,火光冲天而起,把半个天空都映红了。
一个浑身是血的探子,连滚带爬地跑到朱棣马前,声音都变了调:王爷!不好了!宫里头,宫里头烧起来了!陛下……陛下自己在奉天殿里举火了!
朱棣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
他最担心的事,还是发生了。朱允炆这个软弱的侄子,在最后一刻,选择了最刚烈的方式。他这是要用一把火,把朱棣永远钉在篡逆的耻辱柱上。
救火!朱棣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快!所有人都给我冲进去救火!活要见人!死要见尸!
他一马当先,冲过了倒塌的皇城大门。身后的士兵们也跟着他,潮水般涌进了这座曾经象征着天下至高无上权力的地方。
02
热。
一股灼人的热浪迎面扑来,带着木头烧焦的噼啪声和人肉烧焦的古怪臭味。
朱棣冲进宫门时,看到的就是一片火海。金碧辉煌的宫殿,现在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火炬。琉璃瓦在高温下炸裂,像冰雹一样往下掉。
太监和宫女们哭喊着,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,有的人身上沾了火,变成一个火球,在地上翻滚、尖叫。
朱棣的士兵们也乱了。一部分人提着水桶去救火,但那点水,对于这样的大火来说,就是杯水车薪。
更多的人,则被眼前这泼天的富贵冲昏了头,冲进那些还没被大火吞噬的偏殿里,开始疯狂地抢掠。
金银器皿、珠宝玉器、古玩字画,所有能拿动的东西,都被他们塞进怀里。
不许抢!违令者斩!
朱棣声嘶力竭地吼着,但没人听他的。在这片混乱和疯狂中,他这个主帅的命令,显得那么无力。
他心里烦躁得想杀人。他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皇宫,一个体面的胜利,不是眼前这个被土匪洗劫过的废墟。
他带着一队亲兵,直奔火势最猛的奉天殿。
奉天殿已经烧塌了一半,巨大的金丝楠木柱子像一根根通红的烙铁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空气烫得让人无法呼吸。
王爷,进不去了!一个亲兵拉住了朱棣的马缰。
朱棣看着那熊熊燃烧的大殿,眼睛都红了。朱允炆,你个小崽子,算你狠!
就在这时,几个士兵从侧面的火场里,拖着几样东西出来了。
那东西黑乎乎的,蜷缩在一起,还冒着烟。他们把东西扔在地上,跪下报告:王爷,在……在殿后的灰烬里找到的,看这袍子的残片,是……是龙袍……
地上是几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,已经看不出人形,像几截被烧过头的木炭。
其中一具的身上,还粘着一小块烧得只剩下几根金线的明黄色布料。
朱棣翻身下马,走到那堆焦炭前。他蹲下身,用剑鞘拨弄了一下。一股恶臭扑面而来,他忍不住别过头。
真的是朱允炆和他的皇后吗?
他不知道,也无法确定。但他知道,他必须确定。
他站起身,脸上挤出一个悲痛欲绝的表情,声音沉重地对周围的人说:陛下和皇后……殉国了。传令下去,以天子之礼,厚葬。
他必须表现出悲伤,表现出痛心疾首。他是来救驾的叔叔,可惜来晚了一步。
演戏,是每个想当皇帝的人的必修课。
但他心里,那根刺,已经深深地扎了进去。他不信。朱允炆那孩子,看着软,骨子里硬。他不像是个会抱着老婆一起烧死的人。
去东宫!朱棣的表情瞬间从悲痛转为冷酷,去看看懿文太子妃!把她和几位小皇子都给我找出来,客客气气地‘请’过来!一根头发都不能少!
东宫,是他大哥朱标生前的居所,也是他大嫂吕氏现在住的地方。
去东宫的路,比他想象的更长。沿途的宫殿,有的在冒烟,有的已经成了空壳子。
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东西,被踩烂的绣花鞋,断了弦的古琴,碎裂的瓷器。
他经过一处小花园,看到一个秋千架还在轻轻晃荡。秋千的踏板上,放着一只做工精致的布老虎。他记得,他那个最小的侄孙,最喜欢玩布老虎。
他的心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。
这些,都是他大哥留下的血脉。现在,他成了这些人最大的威胁。
他甩了甩头,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都甩出去。他告诉自己,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自古以来,通往皇位的路,哪一条不是用白骨铺成的?
快到东宫时,一阵嘈杂声从前面传来。是女人的尖叫,男人的淫笑,还有东西被打碎的声音。
朱棣的脸色一沉,加快了脚步。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他拨开前面挡路的几个乱兵,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。
东宫的庭院,已经不成样子。原本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牡丹花圃,被踩得一片狼藉。汉白玉的鱼缸被打碎了,几条名贵的锦鲤在地上徒劳地蹦跶着。
院子中央,七八个燕军士兵,正围着一群衣衫不整的女眷。
那些女人,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宫里人,现在却像受惊的鹌鹑一样,挤在一起,瑟瑟发抖。
士兵们嘻嘻哈哈地从她们头上拔簪子,从她们手腕上撸镯子。一个年轻的宫女想反抗,被一个士兵一巴掌打在脸上,嘴角流出了血。
而在这群女眷的最前面,站着一个中年妇人。
她穿着一身深紫色的宫装,虽然发髻已经散乱,脸上也沾了黑灰,但她依然挺直了腰板,用一种混合着恐惧和极度愤怒的眼神,瞪着眼前的士兵。
朱棣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吕氏。他的皇嫂,大哥朱标的妻子,当今皇帝朱允炆的亲生母亲。
一个满脸横肉的士兵,大概是嫌吕氏的眼神让他不舒服,骂骂咧咧地伸手就去推她:看什么看!你那皇帝儿子都变成焦炭了,你还端着架子给谁看!给老子滚一边去!
吕氏毕竟是女流之辈,又惊又怕,早已没了力气。被他这么用力一推,嘴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,身体失去平衡,踉跄着就朝前扑倒。
她穿着一双精致的缎面宫鞋,不跟脚,鞋底也滑。
这一摔,结结实实地趴在了地上。
打一个生肖跳井
她下意识地用手去撑地,正好按在一块破碎的瓷碗上。锋利的瓷片瞬间划破了她的手掌,鲜红的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染红了那片青花碎瓷。
王爷!
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。
那几个正在施暴的士兵,回头看到朱棣那张阴沉得能滴出水的脸,魂都吓飞了。
他们手里的金银首饰叮叮当当掉了一地,然后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跪了下来,把头死死地磕在地上,筛糠一样地抖。
整个院子,刹那间陷入了一片死寂。
风吹过,卷起地上的灰尘和纸屑。远处大火燃烧的毕剥声,清晰地传了过来。
朱棣的目光,就那么凝固在趴在地上的吕氏身上。
他记忆里的吕氏,永远是那么温婉、端庄、得体。
她是太子妃,是大明的未来国母。
每次在宫里遇到,她都会带着温和的笑意,微微屈膝,柔声喊他一声四叔。她的声音很好听,像江南的丝竹。
可现在,这个曾经像玉一样温润光洁的女人,就这么狼狈不堪地,满身尘土地,流着血,趴在他的脚下。
那一瞬间,所有胜利的喜悦,所有君临天下的豪情,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朱棣只觉得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滚烫的棉花,堵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挥了挥手,示意身边的亲兵都退到院子外面去。
然后,他一个人,一步,一步,朝着吕氏走了过去。他的军靴踩在碎石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,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上。
院子里所有幸存的宫女、太监,都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他。
他走到吕氏面前,停下,然后缓缓地弯下了腰。
那只刚刚还在挥斥方遒、决定了数万人命运的手,此刻伸了出去,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颤抖,轻轻地搭在了吕氏的胳膊上。
吕氏的身体,在那只手触碰到她的瞬间,剧烈地颤抖了一下,仿佛被烙铁烫到了一般。
朱棣没有说话,只是用着一股柔和但又不容抗拒的力量,将她从冰冷的地面上,慢慢地扶了起来。
吕氏站稳了。她没有哭,也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歇斯底里地喊叫。她只是抬起头,用那双已经哭干了泪水的眼睛,死死地盯着朱棣。
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。
一开始,里面是滔天的恨意,是刻骨的愤怒,是彻骨的绝望。但渐渐地,这些激烈的情绪都沉淀了下去,最后,只剩下一片空洞的,死寂的,像古井一样深不见底的冰冷。
朱棣被这双眼睛看得浑身不自在。他觉得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偷,所有的伪装和借口,在这双眼睛面前都无所遁形。
他想开口说点什么,来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。他想解释,想辩白。但千言万语,到了嘴边,最后只化成了一声沉重而沙哑的叹息。
大嫂,他的声音很低,低到几乎听不见,我实属无奈。
这句话,他说得很真诚。至少,在那一刻,他自己觉得很真诚。
吕氏的嘴角,突然向上牵动了一下。那不是一个笑容,那只是一个肌肉的抽搐,比哭还要让人心寒。
她缓缓抬起那只还在滴血的手,似乎是想擦一下脸上的污迹,但手举到一半,又停在了半空中,微微颤抖着。
突然,她朝前走了一步,整个人几乎贴到了朱棣的身上。
一股混杂着烟灰、血腥和女人身体的幽香,钻进了朱棣的鼻孔。
她把嘴唇凑到朱棣的耳边,用一种极轻、极缓,仿佛是从地狱深处飘来的,带着冰碴儿的声音,一字一顿地,说了一句话。
朱棣脸上的表情,在那句话钻进他耳朵的瞬间,彻底凝固了。
他脸上那点刚刚挤出来的无奈、愧疚,甚至是假惺惺的悲悯,都像一个被打碎的瓷器面具,哗啦一声,碎了一地。
他的瞳孔,在千分之一秒内,猛地收缩成了两个针尖。他扶着吕氏胳膊的手,不由自主地死死抓紧,几乎要捏碎对方的骨头。
他猛地松开手,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,踉跄着向后退了一大步,差点摔倒。
吕氏看都没再看他一眼。
她慢慢地转过身,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,重新挺直了那根几乎要被压断的脊梁。
她抬起没受伤的那只手,慢条斯理地,把散乱的头发重新挽好。
她垂着头,看着自己那条沾满了灰尘和血迹的裙摆,然后就那么一步一步地,拖着沉重的步子,朝着东宫深处,那片更浓、更沉的黑暗里走去。
她的背影,在夕阳的余晖里,被拉得很长,很长。孤单,决绝,像一个走向坟墓的幽魂。
她再也没有回头。
朱棣一个人在武英殿里喝酒。
宫殿刚刚被清理出来,但空气里那股子烧焦的味道,怎么也散不掉。
他面前摆着一坛从宫中酒窖里翻出来的秋露白,是宫里最好的酒。他不用杯子,就那么抱着酒坛子,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。
酒是凉的,但流进肚子里,却像一团火在烧。
道衍和尚走进来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。朱棣的龙袍还没来得及换,就那么穿着一身戎装,坐在地上,靠着一根幸存的柱子,满身酒气。
王爷。道衍躬了躬身。
朱棣没理他,又灌了一大口酒。
方孝孺、黄子澄那些建文的死忠,在午门外跪着,穿着孝服,哭天抢地,说要为先帝殉葬。怎么处置,还请王爷示下。
朱棣终于有了反应。他抬起头,通红的眼睛看着道衍,突然笑了起来。那笑声很古怪,像夜枭在叫。
先帝?他喃喃自语,哪个先帝?
道衍皱了皱眉:王爷……
他跑了。朱棣打断了他,声音很低,却很清晰,我那个好侄儿,他没死。他从地道里跑了。
道衍的脸色终于变了。他快步走到朱棣面前,压低了声音:王爷何出此言?奉天殿里找到的……
那是假的!朱棣猛地把手里的酒坛子砸在地上,酒水和碎片溅了一地。是吕氏说的!她亲口对我说的!
他挣扎着站起来,抓住道衍的肩膀,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:她说,‘朱棣,你睡不稳这龙椅的。他跑了,天下人会用一生去找他,而你,会用一生去怕他’!
他把吕氏的原话吼了出来。那句话,像一条毒蛇,盘踞在他心里,每一个字都在吐着信子。
道衍沉默了。他知道,事情变得比他预想的要复杂一百倍。一个死了的皇帝,和一个失踪的皇帝,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前者是句号,后者是问号,是一个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。
一个妇道人家的气话,当不得真。道衍试图让他冷静下来。
不!朱棣一把推开他,眼神里透出一股子疯狂的火焰,她的眼神,我看得懂!那不是骗人的眼神!那是诅咒!她放出了一个鬼,一个会追着我一辈子的鬼!
他像一头困兽,在大殿里来回踱步。
方孝孺?他突然停下脚步,冷笑一声,他不是想殉葬吗?好!我成全他!不光是他,所有不肯归顺的建文旧臣,有一个算一个,全都给我杀了!
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,带着金属的质感,冰冷而残忍。
我要诛他的十族!我要让他香火断绝!我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看看,这就是跟朕作对的下场!
王爷,不可!道衍大惊失色,如此一来,会失尽天下读书人之心!
人心?
朱棣哈哈大笑,笑出了眼泪,我连我大哥唯一的儿子都容不下,我还在乎什么人心?我要的是他们怕我!我要用他们的血,把朱允炆存在的痕迹,全都给我冲干净!我要让所有人都忘了,曾经有过一个叫‘建文’的皇帝!
03
从那天起,南京变成了一座血城。
朱棣用最酷烈的手段,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清洗。
方孝孺的诛十族,成了悬在所有读书人头顶的一把刀。成千上万的人被牵连,菜市口的地面,被血浸成了黑色。
他废除了建文的年号,下令销毁所有建文朝的官方文书,仿佛要从时间的长河里,硬生生抹掉那四年。
他登基了,改元永乐。登基大典办得极为仓促,也极为血腥。一边是百官在奉天殿的废墟前战战兢兢地山呼万岁,另一边是屠刀在城中此起彼伏地落下。
但他并没有得到安宁。
吕氏那句魔咒一样的话,日日夜夜在他耳边回响。他开始做噩梦,梦里总是一个穿着龙袍的背影,在前面跑,他怎么追也追不上。
他把锦衣卫的权力扩张到了极致。
无数的密探被派往全国各地,伪装成僧人、道士、商人、乞丐,去寻找一个眉间有痣,曾经当过和尚的年轻人。任何一点蛛丝马迹,都会引来一场腥风血雨。
他甚至不惜动用国库,组建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,交给心腹太监郑和,让他下西洋。
名义上是宣扬国威,寻找仙人,但只有朱棣自己心里清楚,他是在派人去天涯海角,寻找那个可能已经逃到海外的侄子。
他变得喜怒无常,猜忌成性。一个眼神,一句话,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整个朝廷,都笼罩在他的恐怖之下。
他开始疏远南京。
这座城市,每一条街道,每一座宫殿,都在提醒他的过去。他决定迁都,迁到他自己的龙兴之地——北平。
他要建造一座比南京更宏伟、更坚固的都城,一座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紫禁城。他要用物理上的距离,来摆脱心理上的梦魇。
岁月流逝。
永乐大帝朱棣,成了一个传说。
他五征漠北,打得蒙古部落闻风丧胆;他疏通运河,连接南北;他编纂《永乐大典》,将中华文脉汇于一炉。
他用赫赫战功和不世伟业,试图向天下,也向自己证明,他才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。
吕氏在迁都前就死了。死在被软禁的深宫里,死得很安静。
她到死,也没有再和朱棣说过一句话。她的死,让朱棣心里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。他再也无法从她口中,得知那句话到底是真是假。
北京的紫禁城,确实比南京的皇宫更雄伟,也更冰冷。
晚年的朱棣,常常一个人坐在乾清宫里,对着堪舆图发呆。他已经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,身上的龙袍显得空空荡荡。
他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江山,却觉得心里空得厉害。
那个叫朱允炆的侄子,他找了一辈子,也怕了一辈子。
他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鬼魂,缠绕着朱棣的整个后半生。朱棣得到的权力越大,功业越盛,心里的那个洞就越大。
这天深夜,他又从梦中惊醒。梦里,他又回到了南京的火场,大哥朱标浑身是血地站在他面前,问他,四弟,我的允炆呢?
他出了一身冷汗,再也睡不着。他披上衣服,走到殿外。北京的冬夜,寒风刺骨。
一个伺候了他几十年的老太监,颤巍巍地端着一碗参汤过来。
万岁爷,喝点热的吧,别冻着龙体。
朱棣接过碗,却没有喝。他看着碗里自己那张苍老而疲惫的倒影,突然问:你说,朕这一辈子,是不是错了?
老太监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头磕得砰砰响:万岁爷说哪里话!万岁爷是千古一帝,功盖三皇,德超五帝……
朱棣摆了摆手,示意他起来。
他仰头看着天上那轮清冷的月亮,月光照得汉白玉的台阶一片雪白,白得刺眼。
他想起了很多很多年前,在南京那片废墟上,他对那个倒在地上的女人说的话。
大嫂,我实属无奈。
那时的无奈,是借口,是伪装,是为了夺取天下的野心披上的一件外衣。
而现在,他成了天下之主,成了孤家寡人。他站在权力的顶峰,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冷和孤独。
他端起碗,将那碗参汤一饮而尽。然后,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庭院,对着满天寒星,用一种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,又说了一遍那句话。
朕……实属无奈啊。
这一次,不再是辩解。
而是一声,发自肺腑的,被权力反噬了一生的,苍凉的叹息。
相遇打一个生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