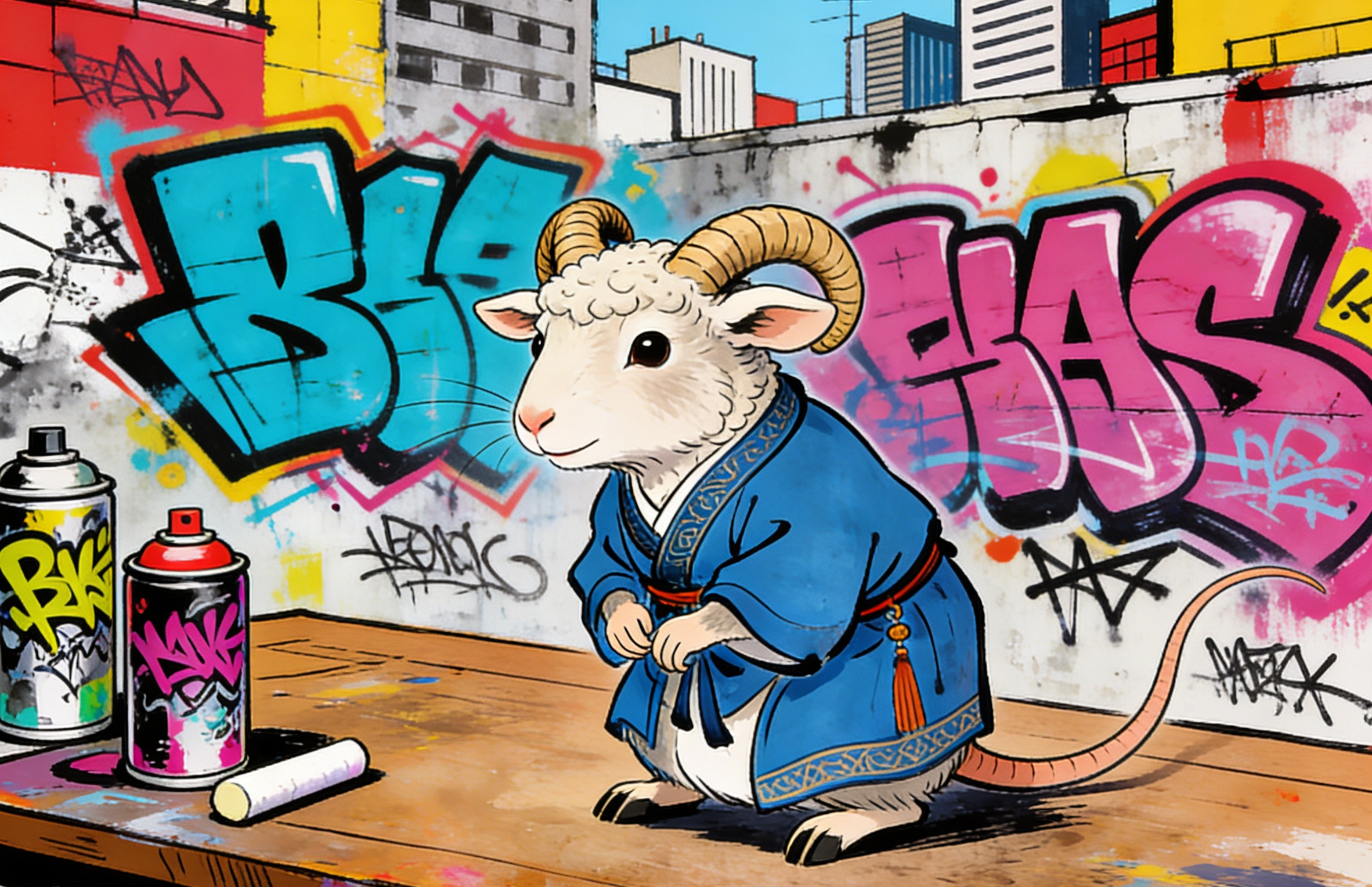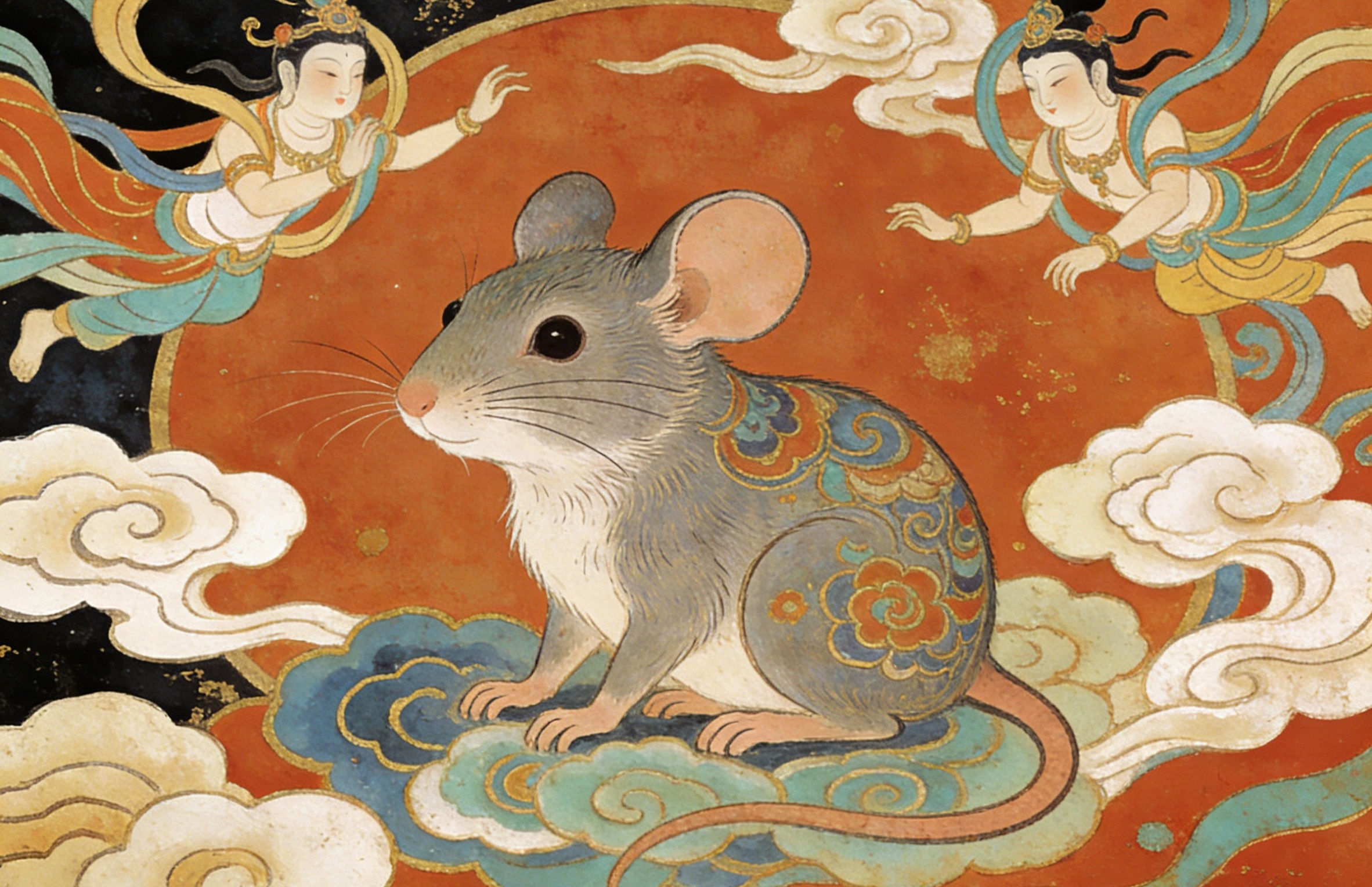阿打一个生肖

文/薛宏新
粪蛋爷蹲在老槐树底下磨锄板,石头蹭着铁,吭哧吭哧地响,像老牛喘气。日头毒得很,村里静得像口枯井,连知了都懒得叫唤。他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磕,火星子溅起几点尘灰。
龙?嘿!粪蛋爷喉咙里滚出一声笑,干涩沙哑,那物件儿,咱庄稼人谁见过真身?可它又无处不在,影子似的,烙在黄历上,挤在十二属相里头,怪不怪?
这话匣子一拉开,树荫底下摇蒲扇的几个老汉都支棱起耳朵。豫北平原上,龙这东西,虚头巴脑,却又实实在在压在老辈儿的心坎上。
早年间,粪蛋爷还是个半桩小子,赶上大旱。天蓝得瘆人,日头像烧红的鏊子扣在头顶上,烤得地皮咧开嘴,庄稼苗子蔫头耷脑,眼见着就熬成了柴火棍。人心都熬焦了,嗓子眼儿冒烟。
求雨喽——!村东头老陈爷一声喊,破了这死寂。那声音抖索着,带着哭腔,穿透了滚烫的空气。男人们光着脊梁,抬出了龙王庙里那泥胎塑像。那龙王爷塑得粗糙,油漆斑驳,龙头上的角都给顽童摸得秃了,却瞪着一双木呆呆的眼睛,瞧着底下跪倒一片的焦渴面孔。
供桌摆在河滩干裂的硬泥地上,几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,清水晃荡着,映着天上那个毒辣辣的日头。粪蛋爷记得清亮,几个村老,满脸褶子挤着汗和灰,嘶哑着嗓子唱念祷词,翻来覆去无非是龙王爷开恩,降下甘霖救救百姓。那调子苍凉悲怆,在空旷的河滩上打着旋。一群光腚娃娃跪在后面,眨巴着懵懂的眼,瞧着大人们磕头如捣蒜。
日头更毒了,河滩的泥味混着汗腥气,直往鼻孔里钻。粪蛋爷那时小,只觉得膝盖跪在滚烫的硬泥上,烙得生疼,嗓子眼干得发不出声。他偷眼去瞧那泥塑的龙王爷,木雕的眼珠子直愣愣望着天上那片无情无义的蓝,毫无动静。三爷心里忽然就冒出一股无名火,直愣愣冲口而出:龙王爷!莫不是你也渴死了?俺们跪着求你,你倒挺尸装泥胎?
话一出口,人群里顿时静得怕人。几个老辈儿吓得脸煞白,哆嗦着要去捂粪蛋爷的嘴。粪蛋爷他爹更是又急又怕,一巴掌扇在他后脑勺上,骂道:作死的小兔崽子!龙王爷也敢编排?!
说来也奇,粪蛋爷这冒失话刚落地不久,西北天边竟真滚过来几团墨黑的云!那云头翻滚着,越积越厚,沉沉地压过来,天色倏地暗了。风也起了,带着一股凉飕飕的土腥味儿,卷起地上的干灰,劈头盖脸地砸向人群。
要下了!要下了!不知谁先喊了一声,河滩上立刻沸腾起来。男女老少顾不得腿麻膝软,全都蹦了起来,仰着脸,张大嘴,贪婪地吸着那带着潮气的风。豆大的雨点砸下来,先是零星几点,噼啪砸在滚烫的地皮上,腾起一股白气,紧接着,哗啦一声,大雨如注,兜头浇下!
浣熊打一个生肖
人群在泥水里欢呼雀跃,蹦啊,跳啊,哭啊,笑啊,像一群疯子。雨水顺着头发、脖子淌进嘴里,又苦又涩,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甘冽。粪蛋爷被他爹紧紧搂在怀里,雨水打得睁不开眼,只听见爹在他耳边吼,声音被雨声盖住大半:小祖宗!你这一嗓子……歪打正着!歪打正着啊!也不知是后怕,还是狂喜。
粪蛋爷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,雨水顺着鬓角流进嘴里,咸咸的,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。他抬起头,透过迷蒙的雨帘,瞥了一眼歪倒在一旁的龙王泥塑。那泥胎被雨水一浇,眉眼模糊,更显出几分笨拙的木然。那一刻,粪蛋爷心里头透亮:哪有什么神龙威严?汉子们脊梁上拱起的汗珠,婆娘们锅底熬干的炊烟,老汉们嘶哑喉咙里挤出的哀告,娃娃们干裂嘴唇上呼出的热气——这才是真正叩开天门、引下雨脚的龙!它不在天上,就在这黄土地里受苦受难、挣扎求生的烟火人间!
看见没?粪蛋爷又磕了磕烟袋锅子,故事讲完了,眯缝着眼看远处起伏的庄稼地,青苗正借着前几日的新雨铆劲儿往上蹿,咱乡里人说的龙性,就是这股子土腥味儿的不服输!旱不死,涝不垮,脊梁骨弯了还能直起来!那庙里的泥胎像个啥?中看不中用的幌子,骗肚里没油水的老实人罢了!真龙的血脉,早化在咱磨锄板的汗水里,渗进犁沟垄背的黄土里了!
风吹过老槐树,叶子哗哗响。老汉们哄笑起来,有人拍着大腿喊:老倔头!你年轻时那愣劲儿,怕不是条孽龙托生的吧?笑声在村子上空滚过,惊飞了几只麻雀。
粪蛋爷也跟着笑,露出豁牙的嘴。他扶着膝盖,慢腾腾站起来,拍拍屁股上的土。远处,他磨好的锄头在日头下闪着青凛凛的光,像一片渴饮了雨水、随时准备破土腾跃的龙鳞。
半青半黄打一个生肖
薛宏新:中共党员。曾出版《小河的梦》《婆婆是爹》《可劲乐》《花间拾趣》《童趣》《鸡毛蒜皮》等个人文集,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故事会》《故事世界》《民间文学》《今古传奇故事版》《传奇故事》《古今故事报》《当代文学》《河南日报》《郑州日报》《安阳日报》《平顶山晚报》《焦作晚报》《新乡日报》《林州文苑》等数百家报刊网络平台,《河南科技报》发过3个文学专版、《作家文苑》发过一个专版、《聪明山文艺》发过2个专刊、《当代文学》海外版发过散文专辑。为《临明关文学》《聪明山文艺》副主编、《现代作家》特约作家、编委,河南省原阳县乐龄书香团成员,原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美名打一个生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