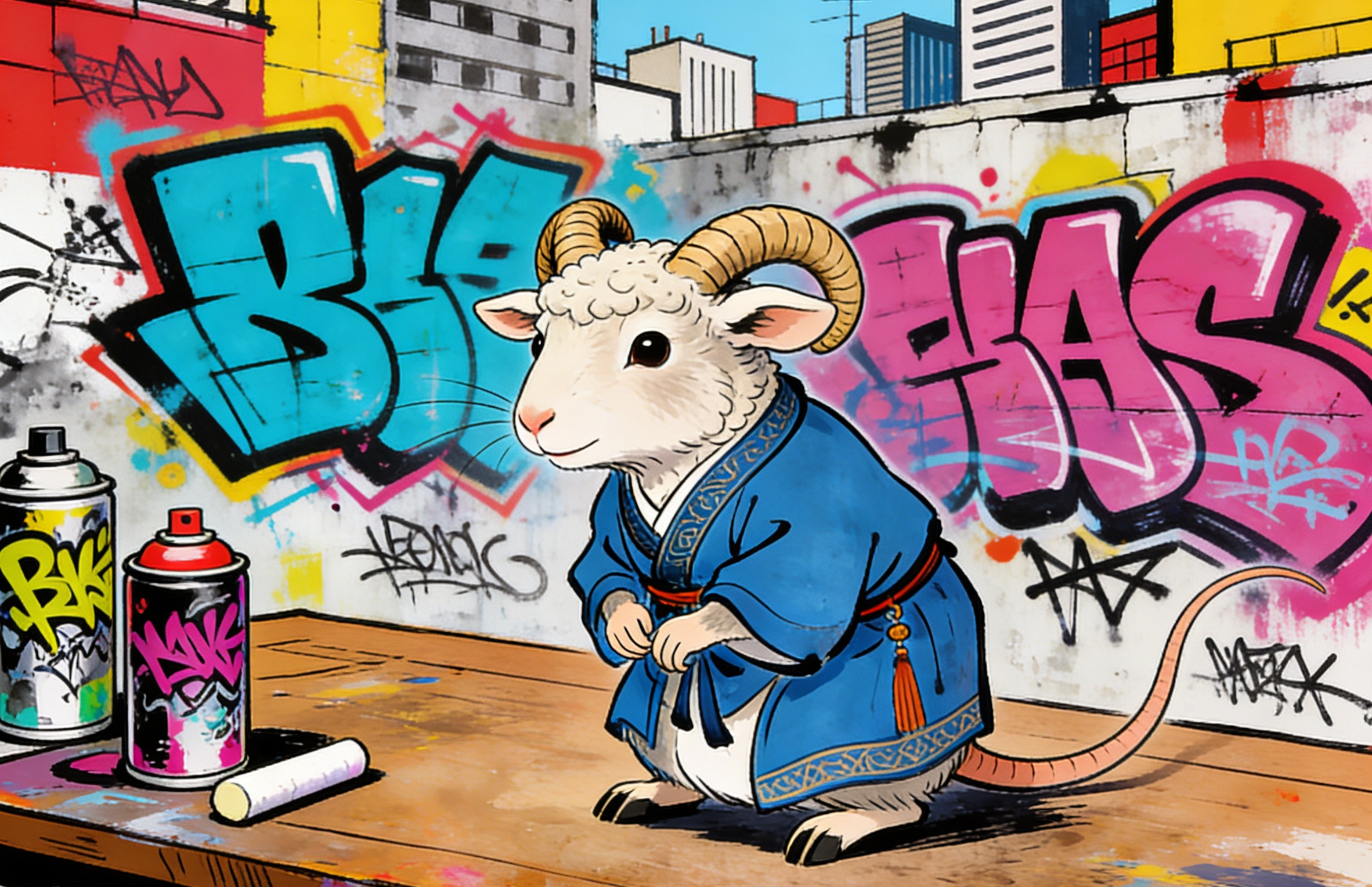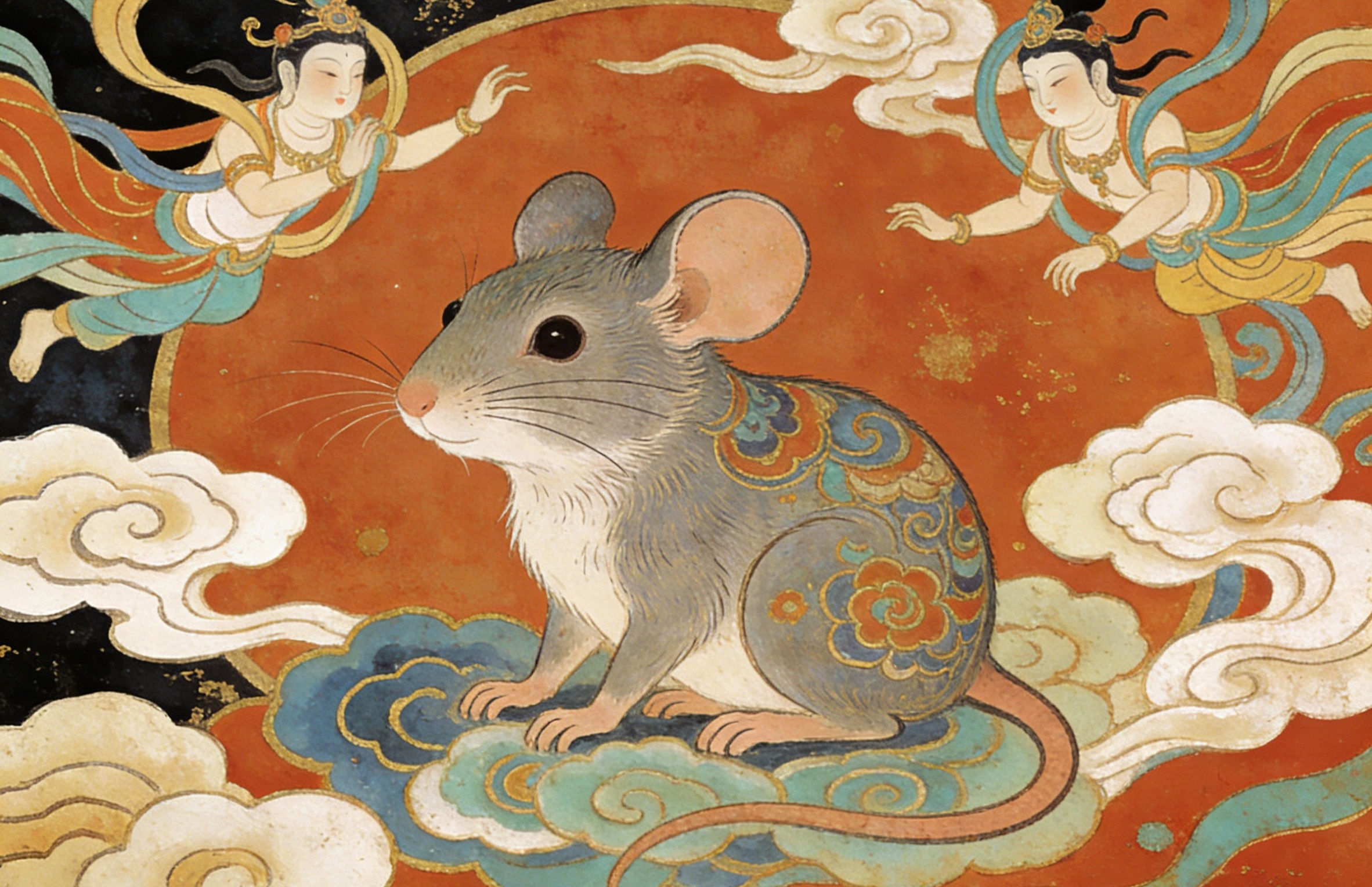的 打一个生肖

作者:钟 倩
继2013年出版《黄雀记》后,作家苏童近期推出长篇新作《好天气》,引发了文坛不小的反响。故事以江南城郊结合部的咸水塘为背景,围绕两个在医院偶然相遇家庭的恩怨展开,以细腻而绵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氤氲潮湿江南水汽的市井日常画卷。苏童将荒诞叙事发挥到极致,以寻找萧好福埋下草蛇灰线,用亦真亦幻的日常寓言为精神迷失者招魂,既是全面反映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江南社会的变迁史和心灵史,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重构之作。
《好天气》共分六章,上半部分侧重鬼怪赋魅,下半部分聚焦时代去魅。从体量上看,苏童历时11年创作完成的47万字大部头,品读起来没有想象中的丝滑感,但从内容上说,小说叙事极具文本敞开性和象喻性,如一座年代久远又瑰丽复杂的记忆宫殿,四面八方的门都可进入,承载多元的阐释空间和丰沛的精神内涵。
灵魂的冒险
智利小说家罗贝托·波拉尼奥说过: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,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,须得过坟场,对视鬼魂。对视鬼魂,意味着与灵魂深处平等对话。倘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,好天气是作者苦心孤诣设置的谜底,一路升级打怪、迂回破案,最终是为了坐拥命运的好天气,即抵达艺术层面万象毕呈的完整的谐和(李健吾语)。
小说开篇即直奔主题,位于郊区一隅的咸水塘,蕴藉深邃而多元的隐喻:咸水塘出名的彩色天空,源自多种颜色的工业烟雾。五种颜色的天空,夯实好天气的精神底色,同时为小说投下诗性光芒——它是荒诞的、迷离的,也是神秘的、诡异的。它的孕育、变幻、冲撞、消失,对应着天空下人们的悲苦遭际。
俨然,这部小说具有精神自传的性质,作者自称小时候在苯酐气中长大,让人极易联想到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的声音与气味。而酸天气、绿眼泪、白蝴蝶、黑金龙、同名母亲、失踪男孩,串联起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从叙事策略分析,苏童以塘为界,聚焦城区街道蒲招娣与塘西乡下黄招娣两个家庭的偶然交集,因祖母一口带福字的棺材引发一连串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,棺木被砍、祖坟被掘,如一根隐形的导火索,点燃了两家的矛盾冲突。
毫无疑问,荒诞叙事是对苦难人间的艺术呈现。自短篇小说《樱桃》起,苏童就开始尝试探寻灵异密码,上承古典文学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之精神血脉,下接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、福克纳《喧哗与骚动》、君特·格拉斯《铁皮鼓》之西方叙事,包括《西瓜船》在内的所有短篇小说似乎都是为《好天气》清理外围、做好铺垫,以完成埋藏心底的一桩夙愿:重返童年。溯源他的文学精神谱系,香椿树街作为始发站,从《米》《河岸》开始起步,至《黄雀记》飞起来了,而《好天气》不啻于一种折返跑后的勇敢越界,他比过去更轻逸、繁复、幽深,也就更加的沉重、斑斓、奇异。
苏童擅长以轻驭重,以肉写灵,以幽暗写光明,以纷繁抵达纯净。他深谙人性渊薮的种种可能性,以鹅的精神意象打开一扇生死之门,祖母之死、土葬骗局、坟墓被掘,七奶奶之死、秋红之死等,继而带出复杂的历史现场和各种离奇的死亡。来自塘西的人生课,总是从死亡出发,到死亡结束。塘东招娣去塘西招娣家讨要婆婆的棺材钱,从此两家结下不可调和的冤债,蒲招娣背负导致萧好福失踪的罪名与舆论讨伐,本是杀鹅陪祭祖母邓罗氏,孰料它参与了祭祀、封坟全过程,直到完成一个长孙的叩首。
鬼鹅通人性,自带毛茸茸的真实,能够看见被遮蔽的真相,它推动小说不断转场、情节承上启下,同时与北方驼子的出场构成某种互文关系。萧好福的归来去注定是个无解的谜,作为中间人的驼子,为精神异化注入另一重视角:好福神奇现身。驼子与鹅相依为命,他那盛满各式玩具的百宝袋,仿佛施了什么魔法,加固了与三个塘西村男孩的友谊堤坝。驼子被驱离,好福回来了,好福又不见了,苏童以双重视角写出了人性的脆弱、无能与噬骨的恐惧,字里行间回荡着内省式的批判和反思,这是成熟作家超越文本经验的练达之处,也是童年视角的二次开掘。
小说结尾处,她最后对着远去的鹅说了声,圣诞快乐。她关上门,兜着那鲫鱼往厨房走,又对着我们家厨房的风光说,年年有余,年年有余啊。与其说这是鹅的最终归宿,毋宁视作咸水塘人的圆满之境,体现中国传统叙事的圆形结构。
萧家姐妹新生记
好的长篇小说胜在细节的编织。《好天气》堪称人鬼情未了的现实主义荒诞史诗,但感人之处在于人物的立体刻画。汪曾祺先生在《晚翠文谈》中谈道:气氛即人物。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,那种阴郁的、潮湿的、惆怅的,甚至令人窒息的氛围。令我过目不忘的是作者对手部的细描,很好地凸显日常性和世俗性。一处细节是联防队顾小宽用手铐威胁好英致伤;另一处细节是塘东菜市场姐妹俩的鱼摊前,豁嘴媳妇以同情一家人的名义购买螺蛳,却习惯多抓一把到自己篮子里,好英的那双手稳稳地扳平一局。所以,后来姐妹俩离家去南方闯荡赚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,而姐妹俩做生意发家暴富后回到咸水塘,在环球水泥厂上建起环球殡葬工业园,这不啻于人世轮回和精神新生。
荠打一个生肖
细节里面住着神灵。黄招娣和蒲招娣同时去回春堂找翁先生看病,一个看耳疾,一个治眼病。翁先生却误把她们当成同一人,连脉息和脉气都一模一样。离开时,天井处两朵被雨打湿的蟹爪菊,构成一种恰到好处的镜鉴关系,苏童的烘云托月手法巧妙且娴熟:蒲招娣举起伞尖用力将它们分开:那两朵菊花仍然在抗拒,它们卷曲修长的花瓣颤抖着,更加紧密地簇拥在一起。当一朵菊花躺在地上,蒲招娣又捡起放回盆里,一句这菊花养得真好,讽刺至极,如凭空一记耳光响亮。
神偷客打一个生肖
《黄雀记》的一粒种子
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有个著名的艺术三因素理论:即种族、时代、环境。种族是植物的种子,蕴藉全部的生命力,而环境和时代就像自然界的气候,起到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作用。显而易见,《好天气》是《黄雀记》的一粒种子,经过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发酵,向上拔节,站成一棵树的静默与生机。他始终从未离开香椿树街枫杨树乡的文学版图,彩色天空下,萧好福的失踪、归来、梦游、又离开,驼子与鹅共居的怪诞,恍若童年的自由穿梭,为精神迷失者招魂的同时,也是为自己失去的、碎片的、痛切的过往进行清算。
近年来,文坛知名作家的返场新作层出不穷,自带挖一口深井的心力和坦诚,譬如,毕飞宇《欢迎来到人间》、格非《登春台》、麦家《人生海海》等,但是不少读者难以接受的是作家对自我的重复,背后乃是思想的疲惫滑行,故事的移花接木。特别是碎片化读屏的今天,读者对审美的要求不是降低了,反而是不断提出新的要求。
不得不说,《好天气》也难以脱离这样的诟病。从结构上分析,外篇篇外篇与余华《文城》后半部分极为相似,补笔着墨较多,其中小说第四章我母亲的三次求诊,情节拖沓极易导致审美疲劳;而鬼鹅形象与作家路也长篇小说《午后的空旷——仲宫镇童年》中,小何子叔叔宿舍里养的猪何粉红形象异曲同工,何粉红最后进了厂里食堂,而咸水塘的鬼鹅温情消失,两者皆有浓重的悲剧色彩。
苏童此次新作深度开掘和回望童年,借用魔幻和灵异的指挥棒搅动城北旧事,在好天气下激烈冲撞、旋即混淆,于《咸水塘相对论》所谓偶然与必然、内因与外因中走向圆满境界——萧好莉怀上了邓家的骨肉,暗喻咸水塘的明媚未来和美好生活。
(作者系青年评论家)
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长跑,一直写到最后,不知不觉写了100万字,把我自己都吓着了,然后我对自己说,这个小说不要有100万字。然后我就一直删改,一直修改压缩,不停地调整,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本。
最早的时候,小说叫作《咸水塘史》,但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时,提到这部小说,北方的同学们都很迷茫,他们不懂什么是‘塘’的概念。我后来想来想去,小说里有很多种天气,不如就改名叫《好天气》。
我脑子里有一个坐标——平面上是乡村与街道的对称,人物上是两个‘招娣’和她们孩子的故事。还有天空的黑与白、气味的酸与苦……各种对峙,反映了初始的街道文明和传统的乡村文明之间的矛盾与融合。
我从小生长的环境,就是街道、工厂、农田。这个小说是我个人真实生活经历最多的,因为我确实生活在工厂区,比如小时候我看到的黑天气,彩色的天气,白天气,别人以为是我想象的虚构的,其实都是我看到过的。
我的短篇小说尽管写的都是中国的事情,但如果用一种乐器来表示,用的都是西洋乐器,有的像钢琴,有的像小号、圆号。在写《好天气》的时候,如果仍然用乐器比喻,我会大量地使用民族乐器,里面有唢呐、二胡、笛子、箫等等。审美是一种固执,其实也是一种坚持。
——苏童
来源: 文汇报
腔打一个生肖动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