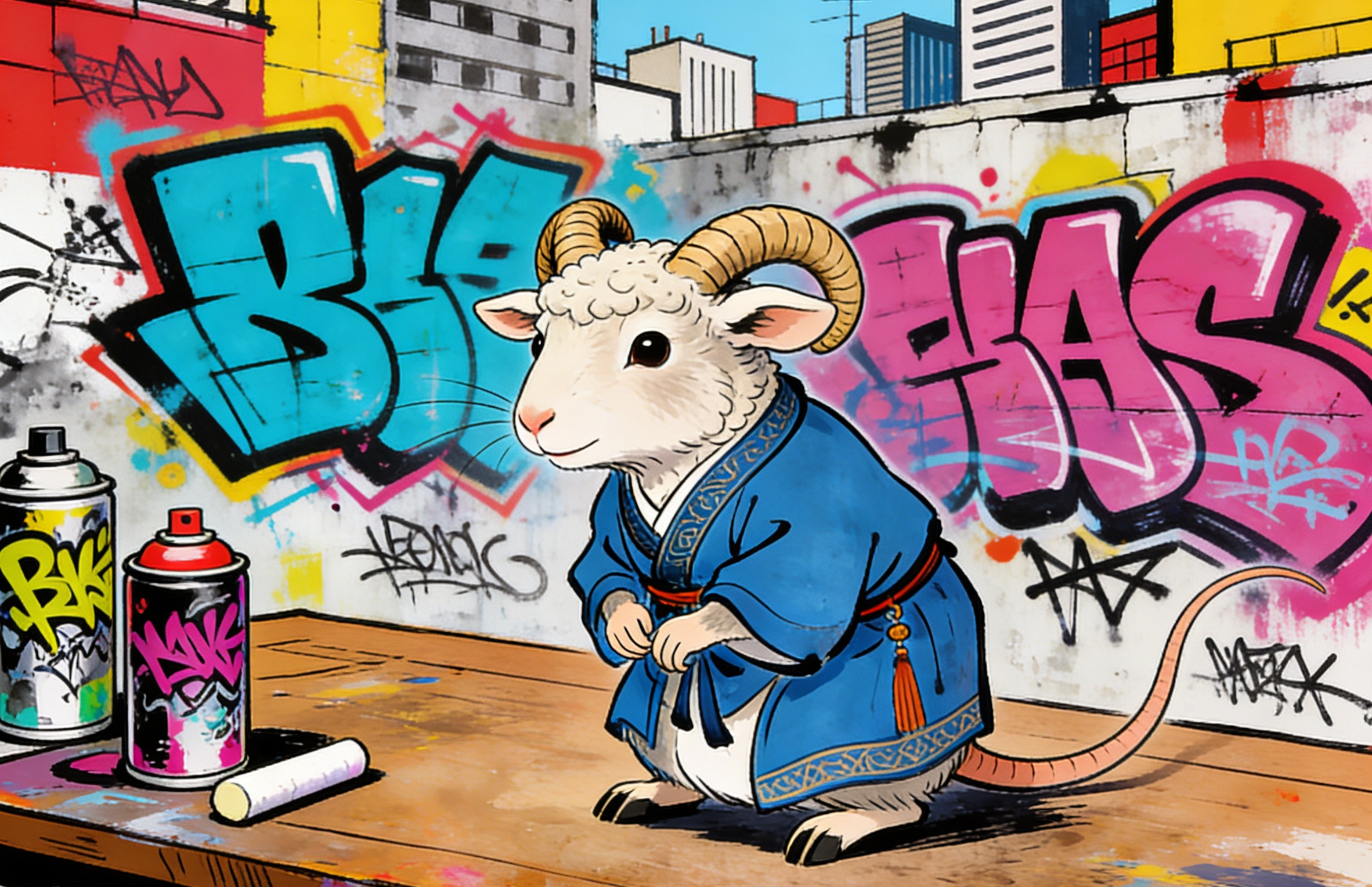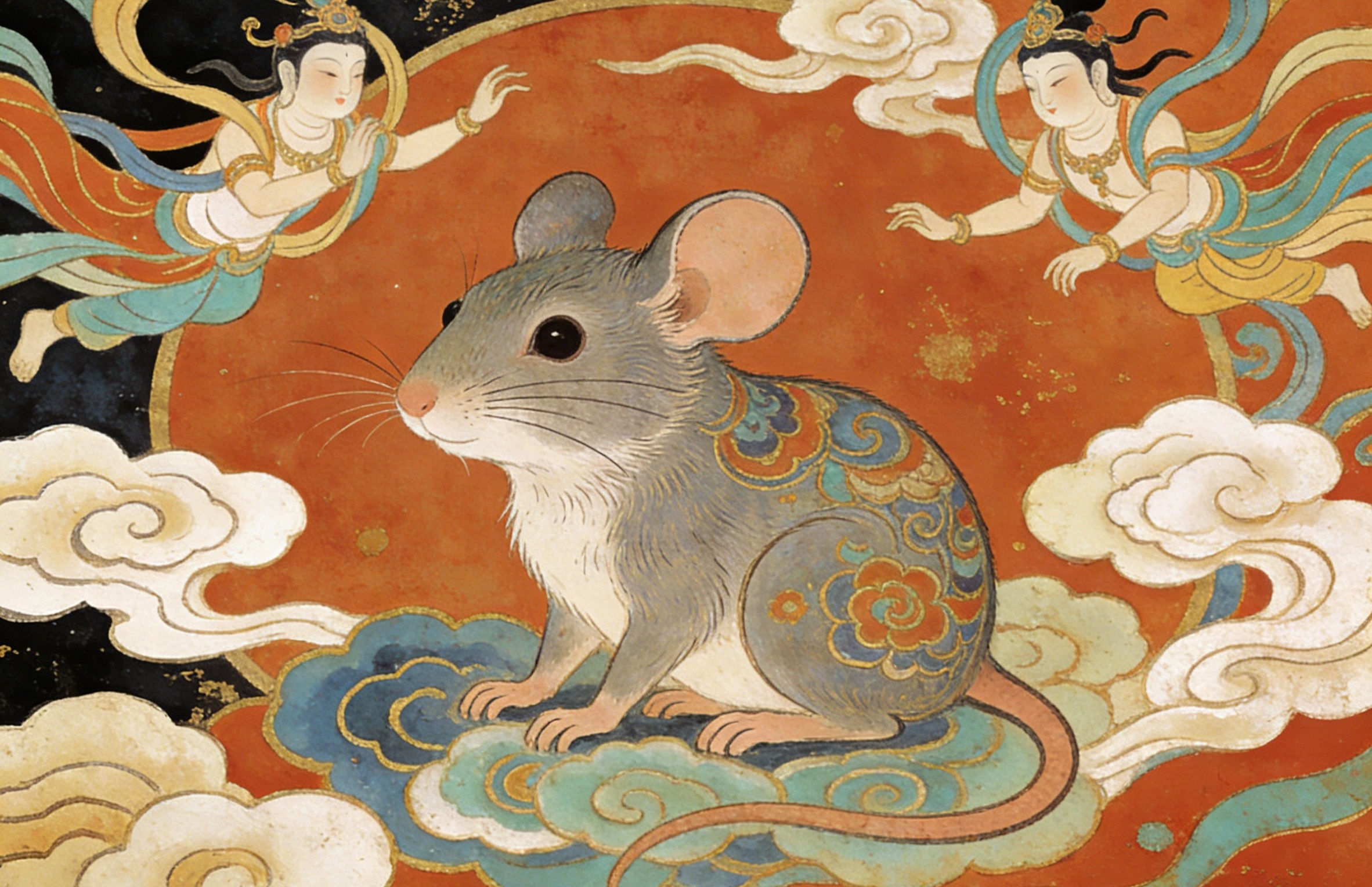圆桌猜打一个生肖

邻里之间,真的能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,甚至子孙后代的旦夕祸福吗?
易经有云: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天地万物,皆在阴阳五行的流转之中,相生相克,互为表里。人居于天地之间,自然也逃不开这无形的罗网。
宅邸是人的安身之所,如同鸟之巢穴,兽之洞窟,是气运汇聚的根本。而邻里,则是宅邸之外延伸的气场,是影响这方水土最直接的变数。
古人常言千金买宅,万金买邻,这句话的背后,难道仅仅是人情世故的考量吗?或许,它还隐藏着更为深邃的,关乎气数与命理的玄机。
相传,蜀汉丞相诸葛亮晚年,曾将毕生所学之奇门方术、观星望气之法,融入一部名为武侯宅经的残卷之中。此书不谈金瓦红墙的富贵,不论雕梁画栋的奢华,只论一事:如何通过邻里之间的生肖格局,为家中引来贵气,催发文昌,令子孙出人头地,光耀门楣。
其中,对于金鸡之命,也就是生肖属鸡的人,更是留下了极为隐秘的批注,道出了三种能与其形成贵子格局的生肖邻居。这究竟是确有其事的古贤智慧,还是后人穿凿附会的无稽之谈?在岫岩县的一户宋姓人家身上,这个谜题,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,缓缓展开了。
01
岫岩县的宋勤孝,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庄稼汉。
他这辈子,就像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,粗糙、本分,却也抓不住什么真正的好光景。
人过四十,两鬓已染上了秋霜,住的是三间祖上传下来的土坯房,守着几亩薄田,日子过得不咸不淡,像一杯温吞的凉白开。
勤孝,勤孝,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,就是盼着他能勤劳孝顺,安稳一世。他也确实做到了,侍奉双亲归山,与妻子杨氏相敬如宾,唯一的指望,便是七岁的儿子宋文远。
这孩子,是宋勤孝半辈子的心头肉。
文远不像村里其他的野小子,不爱上树掏鸟窝,也不爱下河摸鱼虾,偏偏就爱抱着几本破旧蒙学书卷,一看就是半天。
过路的秀才曾夸他眉眼清秀,有几分读书人的灵气。宋勤孝听了,心里就像喝了蜜,转头看见儿子那略显单薄的身子和时常泛黄的脸蛋,又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。
文远的身子骨,太弱了。三天两头不是风寒,就是咳嗽,药罐子几乎就没断过。
宋勤孝愁啊,他属鸡,听人说属鸡的人命里带金,性子要强,可他这只鸡,却仿佛被困在了一个破旧的篱笆院里,怎么扑腾,也飞不起来。
他把所有的希望,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。他总觉得,只要儿子能有出息,自己这辈子的辛苦,就都值了。
这年秋后,庄稼收了仓,天一日比一日凉。村里来了一个摇着拨浪鼓的货郎。这货郎与旁人不同,不光卖些针头线脑,还夹带些不知从哪淘换来的旧书古籍。
宋勤孝那天正好揣着几个铜板,想给儿子扯块做新衣的布料,眼角余光却瞥见了货郎担子里的一本蓝皮旧书。
书皮上,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着四个大字武侯宅经。
武侯?宋勤孝心里一动,那不是说书先生口中,能呼风唤雨、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吗?
他鬼使神差地放下布料,拿起那本书,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墨香扑面而来。
店家,这书怎么卖?
货郎瞥了他一眼,伸出两个指头:二十文,一文都不能少。这可是宝贝,讲的是风水堪舆,能改换门庭的!
二十文,够给文远买两剂上好的汤药了。
杨氏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衣袖,低声道:当家的,买这没用的东西干啥?还是给孩子抓药要紧。
宋勤孝却像是着了魔,他翻开书页,一行字瞬间攫住了他的目光:金鸡遇邻,三合成局,贵子自出,门楣光耀
金鸡,说的可不就是自己吗?
贵子自出
这四个字,像一道惊雷,在他心头炸响。他一咬牙,数出二十个铜板,将那本武侯宅经揣进了怀里,布也不买了。
回到家,杨氏一边叹气,一边去熬那半包陈药。宋勤孝则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房里,点上油灯,贪婪地读了起来。
这书写得半文半白,艰涩难懂。但宋勤孝识得几个字,连蒙带猜,竟也看明白了大概。
书里说,一个人的气运,不仅关乎自身命理,更与所居之地的风水,尤其是邻居的气场息息相关。
特别是属鸡的人,五行属金,其性锐利,但也易折。若邻里不合,气场相冲,便会家宅不宁,子嗣孱弱,好事多磨。
宋勤孝看到这里,手心不禁冒出冷汗。
他家的邻居,就两户。
东边,是铁匠王屠户。王屠户人高马大,一脸横肉,整日叮叮当当地打铁,脾气火爆。宋勤孝曾托人问过,这王屠户,属牛。
书上说,酉鸡与丑牛,虽是三合之一,但牛性倔,鸡性傲,若无调和,反成斗局,日日纷争,耗损锐气。
宋勤孝一想,可不是吗?王屠户家的炉烟,一刮风就全飘进自家院里,呛得人咳嗽不止。平日里,更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没少口角。
西边,是寡妇李三娘。李三娘是个碎嘴的,东家长西家短,整日搬弄是非。宋勤孝记得清楚,她属狗。
书上赫然写着:金鸡遇犬,泪双流。此为六害之局,最损家运,主口舌官非,鸡犬不宁。
宋勤孝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了。
一个斗局,一个害局,把他家死死地夹在中间。怪不得自己半辈子一事无成,怪不得文远的身子骨总是好不起来!
原来根子,竟出在了这邻居身上!
他像是找到了所有苦难的源头,既感到一阵后怕,又生出一丝希望。书里既然指出了病根,就一定有解药!
他急切地往下翻,想要找到那能三合成局的另外两种贵人生肖。
可就在这时,屋外突然传来杨氏一声惊恐的尖叫:文远!文远你醒醒啊!
宋勤孝心里咯噔一下,猛地推开门冲了出去。
只见院子里,七岁的文远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双眼紧闭,脸色青紫,嘴角还挂着一丝白沫。杨氏跪在一旁,拼命地摇晃着他,哭得撕心裂肺。
宋勤孝只觉得天旋地转,他几步冲过去,颤抖着手探了探儿子的鼻息,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。
快!快去请张郎中!他冲着已经吓傻的杨氏嘶吼道。
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口,一个更坏的消息,如同雪上加霜,传进了他的耳朵。
隔壁的王屠户一边看热闹,一边幸灾乐祸地嚷嚷道:宋勤孝,你家那点破事还管不过来呢?告诉你个事儿,你家南边那块荒地,被镇上的钱扒皮买下来了!
钱扒皮,大名钱万贯,是岫岩县有名的劣绅,为人最是贪婪霸道,因手段狠辣,人送外号钱扒皮。
宋勤孝的心,一下子沉到了谷底:他买那块地要做什么?
王屠户嘿嘿一笑,露出满口黄牙:还能干啥?听说要建个染坊!染布的臭水,以后就从你家门前过喽!啧啧,这下你家可真是前后夹击,永无宁日了!
染坊!
那刺鼻的气味,那五颜六色的毒水
宋勤孝抬头看了看自家院子,东边是叮当作响的铁匠铺,西边是搬弄是非的寡妇家,如今南边又要建起一个臭气熏天的染坊。
再看看怀里气息奄奄的儿子,他手中的那本武侯宅经仿佛有千斤重。
书上说,要遇贵邻。可如今,他家周围,竟是要被这恶邻围成一个铁桶般的死局了!
难道,这真是天要亡他宋家吗?
02
张郎中来了,捻着山羊胡,一番望闻问切,最后只是摇摇头,开了几副固本培元的方子,叹着气走了。
他说,这孩子的病根,在娘胎里就落下了,先天不足,后天失养,只能慢慢调理,听天由命。
听天由命四个字,像四根钢针,扎在宋勤孝心上。
他不能听天由命!他若是认了命,儿子怎么办?
夜里,文远发起了高烧,小脸烧得通红,嘴里说着胡话,一声声喊着冷。杨氏抱着儿子,眼泪就没断过。
宋勤孝坐在油灯下,双眼熬得通红,死死盯着那本武侯宅经。
书上关于三合贵局的说法,已经被他翻烂了。上面只说金鸡遇成龙虎之势,遇得麟凤之祥,却用几个隐晦的符号代替了那关键的生肖。
他看不懂,但他看懂了另一句话:地劣则人衰,地善则人旺。逢绝地,当速迁之,如避蛇蝎。
迁!必须搬走!
这个念头一旦生出来,就在他心里疯狂地扎了根。
第二天一早,天还没亮,宋勤孝就揣着家里仅剩的几吊钱,出了门。他要把这三间破屋,连同那几亩薄田,全都卖掉。
他要离开这个被恶邻包围的绝地!
然而,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。
村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的情况?东边吵,西边闹,南边眼看就要起染坊,谁会花钱来买这份罪受?
一连几天,上门来看房的人不少,可一听说周围的情况,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有人甚至劝他:勤孝啊,你就认命吧。钱扒皮的染坊一开,你这房子,白送都没人要了。
宋勤孝的心,一点点冷下去。
他甚至厚着脸皮,去找了钱扒皮,想求他高抬贵手,把染坊建到别处去。
钱扒皮坐在太师椅上,端着茶碗,眼皮都没抬一下,只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:宋勤孝,你算个什么东西?也配来跟我谈条件?我钱某人买下的地,别说建染坊,就是建个茅厕,也得你天天闻着!
羞辱,赤裸裸的羞辱。
宋勤孝攥紧了拳头,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。要不是为了病床上的儿子,他真想一拳砸在那张肥胖的脸上。
从钱家出来,他像个被抽了筋骨的木偶,踉踉跄跄地走在回村的路上。
秋风萧瑟,卷起漫天黄叶,拍打在他脸上,冰冷刺骨。
他输了,输得一败涂地。
回到家,看到妻子杨氏那张憔悴的脸,和床上儿子微弱的呼吸,宋勤孝这个七尺高的汉子,终于撑不住了,蹲在门槛上,双手抱着头,发出了野兽般的低吼。
他恨这世道不公,恨自己无能为力。
就在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时,杨氏默默地从里屋走了出来,将一个小布包,塞进了他的手里。
当家的,这是我当年陪嫁的银镯子和一对耳环,你拿去当了吧,应该还能凑点钱。她的声音沙哑,却异常平静。
宋勤孝打开布包,那对银镯子在昏暗的光线下,散发着温润的光。这是岳父岳母留给妻子的念想,她平日里碰都舍不得碰一下。
不这不行宋勤孝的声音在发抖。
没什么不行的。杨氏蹲下身,轻轻握住他冰冷的手,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,只要文远能好起来,这些身外之物,算得了什么?你不是说,要给孩子找个好地方吗?那就去吧。砸锅卖铁,我都跟你去。
妻子的这番话,像一道暖流,瞬间融化了宋勤孝心中所有的冰冷和绝望。
他抬起头,看着妻子布满红丝的眼睛,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有了这笔钱,加上变卖家中所有能变卖的东西,总算凑了十几两银子。这点钱,在县城里买不起房,但在村子偏僻的角落,或许还能找到一处容身之所。
皇天不负有心人。
几天后,一个远房的亲戚传来消息,说村东头靠近山脚的地方,有一处老宅子要出手。
那宅子是村里一户姓周的孤寡老人的,老人前不久过世了,膝下无儿无女,族人便想把宅子变卖了换些香火钱。
宋勤孝跟着亲戚去看房。
宅子很偏,在一条死胡同的最里头,院墙都塌了半边,屋顶上长满了杂草,看上去破败不堪。
但宋勤孝却一眼就相中了这里。
因为这里,安静!
院子左邻,住着一位姓陈的老秀才,据说读了一辈子书,性子孤僻,不爱与人来往,整日在家中读书写字。
院子右舍,住着一位姓马的年轻寡妇,带着个女儿,靠做些刺绣活计为生,为人温和,沉默寡言。
没有叮当作响的铁匠铺,没有搬弄是非的长舌妇,更没有臭气熏天的染坊。
这里,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清净之地!
宋勤孝当即拍板,用所有的钱,买下了这栋破败的宅子。
搬家的那天,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让他受尽折磨的老屋。
一家人齐心协力,修补院墙,清理杂草,把新家收拾得有了一点家的模样。
说来也怪,搬到新家不过十来天,儿子文远的身体,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。虽然依旧瘦弱,但脸色红润了许多,咳嗽的毛病也犯得少了,甚至能下地跟着宋勤孝在院子里跑几步了。
宋勤孝欣喜若狂,他越发坚信,武侯宅经上说的都是真的!
他现在唯一要做的,就是弄清楚这两位新邻居的生肖。
他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。
经过几番旁敲侧击,他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,右邻那位姓马的寡妇,属蛇。
蛇!
宋勤孝的心狂跳起来。
他清楚地记得,书上那句金鸡遇,后面的符号,其中一个的注解,正是巳蛇!
酉鸡、巳蛇书上说,这是三合贵局里至关重要的一环!
他找对地方了!
宋勤孝激动得浑身发抖,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儿子成才,家门兴旺的未来。
现在,只要再确定那位陈老秀才的生肖,如果他恰好是书中所指的最后一个关键生肖,那这贵子之局,就成了!
然而,就在他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,一个他从未注意到的细节,让他如坠冰窟。
一日深夜,他起夜,无意中发现,自家后院那堵破败的土墙之外,竟然还有一间矮小的,几乎要塌掉的茅屋。
那茅屋黑黢黢的,像是早已荒废。
可就在他准备转身回屋时,一阵若有若无的,极富韵律的笃、笃、笃声,从那茅屋里传了出来。
声音很轻,很慢,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,显得格外诡异。
宋勤孝的心,猛地揪紧了。
这破墙之后,竟然还住着第三户人家?
03
那阵笃笃声,像一把小锤,一下下敲在宋勤孝的心上。
他搬来这么久,竟从未发现后院还藏着这样一户人家。这家人是谁?他们是这贵子之局的一部分,还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?
接连几个晚上,宋勤孝都难以入眠。他悄悄趴在后院的墙头,借着月光,只能看到那间茅屋一个模糊的轮廓,以及从门缝里透出的,一丝微弱如豆的灯火。
那笃笃声,每到深夜子时,便会准时响起,像是在雕刻着什么东西,又像是在进行某种不为人知的仪式。
妻子杨氏看他日日神情恍惚,忧心忡忡地问他出了什么事。
宋勤孝不敢说实话,他怕妻子说他痴迷鬼神,胡思乱想。他只能含糊其辞,说自己还在为生计发愁。
可喜的是,儿子文远的状态越来越好。
左邻的陈老秀才,偶尔会在院子里踱步吟诗。文远便趴在墙头上,听得入了迷。几次之后,陈老秀才注意到了这个灵气的孩子,竟主动招手,让文远过去,考校他几个字。
一来二去,老秀才竟对文远喜爱有加,时常会送些笔墨纸砚过来,还指点他读书习字。
看着儿子在老秀才的教导下,一天比一天沉稳聪慧,宋勤孝的心里,既是欢喜,又是焦虑。
欢喜的是,儿子似乎真的走上了贵子之路。焦虑的是,那个神秘的第三位邻居,始终像一根刺,扎在他心底。
他必须弄清楚那人的底细和生肖。
这天,他鼓起勇气,绕到后院的茅屋前。
门是虚掩着的。他轻轻推开一道缝,一股混杂着潮气和木头屑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屋里很暗,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背影,正佝偻着身子,坐在一张小木凳上,专注地雕刻着手中的一块木头。
袁字打一个生肖
那人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破烂衣衫,头发像一蓬枯草,乱糟糟地披在肩上。
牛蛙打一个生肖
听到门响,那人猛地回过头。
宋勤孝看到了一张让他永生难忘的脸。那是一张被生活折磨得几乎脱了相的脸,两颊深陷,颧骨高耸,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,充满了警惕、孤僻,甚至是一丝疯狂。
你看什么?滚!那人发出沙哑的低吼,像一头被惊扰的野兽。
宋勤孝被他眼中的凶光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。
他想问些什么,但话到嘴边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回到家中,他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
他向村里人打听,才知道那茅屋里住的,是个无名无姓的木雕匠,村里人都叫他疯阿七。
据说,疯阿七年轻时曾是县里有名的木雕师傅,一手雕龙画凤的绝活,出神入化。后来不知为何,得罪了官府,一夜之间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他便疯了,躲到这村子最偏僻的角落,苟延残喘。
至于他的生肖,没人知道,也没人关心。
一个疯子,一个败落的匠人
宋勤孝的心,凉了半截。
这绝不是他期望中的贵邻。这人的身上,没有一丝一毫的贵气,反而充满了衰败和疯狂的煞气。
难道,自己千辛万苦,躲开了斗局和害局,却一头撞进了一个更可怕的败局?
他开始怀疑,怀疑那本武侯宅经,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。
是不是从一开始,就错了?
就在他心灰意冷,几乎要放弃的时候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
左邻的陈老秀才,因为年事已高,感染了风寒,一病不起。
宋勤孝和杨氏念着老秀才教导儿子的恩情,每日轮流过去照料,端茶送水,煎药喂饭,比亲儿子还要尽心。
半个月后,老秀才的病,总算有了起色。
一日,他把宋勤孝叫到床前,拉着他的手,老泪纵横:勤孝啊,若不是你们夫妇,我这把老骨头,怕是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这份恩情,老夫无以为报
宋勤孝连忙说:先生言重了,您教导文远读书,我们感谢还来不及。
老秀才喘了口气,看着窗外,眼神变得悠远起来。他缓缓说道:我观文远这孩子,是块璞玉,只是需要良师雕琢。老夫不才,愿收他为弟子,倾囊相授。将来,能否博取功名,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
宋勤孝闻言,激动得差点跪下。
这可是天大的喜事!陈老秀才虽然一生未仕,但学问在岫岩县是出了名的。能做他的入室弟子,文远的未来,等于有了一盏明灯!
他语无伦次地道着谢,激动之余,不免又想起了自己那块心病,便试探着提起了后院那个疯疯癫癫的木雕匠。
先生,您可知,我们后院那个疯阿七他究竟是何来历?
听到疯阿七这个名字,陈老秀才原本浑浊的眼睛里,竟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光。
他沉默了许久,才长叹一声。
他不叫疯阿七。老秀才的声音变得异常凝重,勤孝啊,你可知画龙画虎难画骨?你看人,亦是如此,不能只看皮相啊。
宋勤孝一愣,不解地看着老秀才。
老秀才定定地望着他,一字一句地说道:你费尽心思,想要凑齐武侯宅经上的三合贵局,对也不对?
宋勤孝心中剧震,如同被人窥破了最大的秘密。
老秀才却摆了摆手,示意他坐下,继续说道:你的心思,我早已看穿。右邻属蛇,以固根基,此为一步好棋。但你以为,这贵局,仅仅是凑齐三个生肖那么简单吗?
他摇了摇头,眼中带着一丝怜悯和睿智。
你错了,大错特错!武侯之智,鬼神莫测,他留下的经文,又岂是凡夫俗子能一眼看透的?那所谓的三合,并非指简单的生肖凑合,而是一种更为深奥,更为玄妙的人与势的格局!
老秀才深吸一口气,像是要说出一个惊天的秘密。
那属蛇的邻居,确实是其中一角,但她的意义,并非只是生肖为巳那么简单。而你心心念念的另外两个贵邻,你更是从一开始,就完全想错了方向!
宋勤孝如遭雷击,呆立当场。
他感觉自己所有的认知,在这一刻被彻底粉碎。那本被他奉为圭臬的武侯宅经,原来根本不是他所理解的那样。
什么生肖相合,什么气运之说,在老秀才的话语里,似乎都成了最肤浅的表象。
先生此话何意?他的声音因为震惊而变得干涩沙哑。
陈老秀才的目光穿透了窗棂,仿佛看到了某种命运的轨迹,他缓缓道:武侯设下的,从来不是一个公式,而是一个谜题,一道考验人心的智慧之局。他要找的,不是三个特定生肖的傀儡,而是三种具备特定势的人。
那右邻马氏,其生肖为蛇,固然是。但她真正的势,在于静与韧。她于逆境中默然安守,以柔克刚,这便是地龙蛰伏之象,为你的金鸡之命,提供了最坚实的土地,使其锐气不至于虚浮漂泊。这,才是这第一位贵邻的真正含义。
宋勤孝的大脑一片空白,他从未想过,一个邻居的生肖背后,竟还藏着如此深远的寓意。
老秀才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,他盯着宋勤孝,话锋一转,直指核心:至于另外两位贵邻,更是与你所想的天差地别。其中一位,并非在你的宅邸之外,而在你的宅邸之内!而另一位,就是你避之不及的那个疯阿七!
这一番话,如洪钟大吕,震得宋勤孝头晕目眩。
局中之局,谜中之谜。
诸葛武侯真正的智慧,原来并非简单的生肖排列,而是一盘关乎人性和格局的惊天大棋。那被他误解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贵邻,究竟代表着怎样的势?他们又分别是哪两种截然不同的生肖,以何种匪夷所思的方式,共同构成了那传说中能让家中必出贵子的至上格局。
04
宅邸之内的贵邻?
宋勤孝下意识地环顾自己这间破败的屋子,除了自己,就是妻子和儿子,哪里还有第四个人?
先生,您是说
老秀才打断了他,反问道:勤孝,我问你,在你最绝望,最无助的时候,是谁给了你最后一根救命稻草?是谁让你在天寒地冻之时,心中还能燃起一丝暖意?
宋勤孝一怔,脑海中浮现出的,是妻子杨氏那双布满红丝,却无比坚定的眼睛。
是她,在他被钱扒皮羞辱,走投无路,蹲在门槛上像野兽一样嘶吼时,默默递上了自己陪嫁的银镯子。
是她,在他卖房无门,心灰意冷时,用沙哑的声音说出砸锅卖铁,我都跟你去。
是她,是杨氏!
是是我的妻子,杨氏。宋勤孝喃喃道。
老秀才欣慰地点了点头:正是。你这只金鸡,性子高傲,锐气十足,一心只想往上飞。可你有没有想过,若无大地承载,若无暖风相助,再锐利的翅膀,也只能在原地扑腾,耗尽心力。
你的妻子杨氏,她属什么?
宋勤孝猛地想起来,杨氏属龙!辰龙!
她属龙
老秀才抚掌一笑:这就对了!武侯宅经中第二个隐晦的符号,注解的正是辰龙!但武侯真正的深意,并非让你去寻一个属龙的邻居。你想想,龙凤呈祥,龙与鸡,本就是六合之贵。真正的贵龙,又怎会远在天边?
你的妻子,便是你家中那条潜龙!她的势,是容与升!她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,包容了你所有的冲动与落魄;她用自己的牺牲与奉献,化作一股向上的暖流,托举着你高飞的梦想。你只知向外求助,却不知自家后院,就藏着一条真龙啊!
宋勤孝的眼眶瞬间红了。
他想起这些年,杨氏跟着他受的苦,吃的亏,却从未有一句怨言。他为了儿子,为了那本破书,魔怔了一般,却忽略了身边这个默默付出一切的女人。
他自以为是家里的顶梁柱,却不知,妻子才是撑起这个家,不让它垮塌的真正基石。
原来,这第二位贵邻,竟是自己的妻子!
所谓万金买邻,最该用万金去珍惜的,原来是自己的枕边人。
宋勤孝心头百感交集,悔恨、感激、愧疚,五味杂陈。他对着老秀才,深深地鞠了一躬:先生,我我明白了。
明白就好。老秀才扶住他,现在,你还觉得后院那个疯阿七,是个败局吗?
05
提及疯阿七,宋勤孝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妻子是潜龙,马寡妇是地蛇,一升一静,已是难得。可那个疯疯癫癫,满身煞气的木雕匠,又能代表什么势?
他实在想不通,一个家破人亡的疯子,如何能成为贵子之局的关键一环。
先生,恕我愚钝。宋勤孝恳切地问道,那疯阿七,他
老秀才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又抛出了一个问题:勤孝,你属鸡,金鸡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?
是是它那一身华丽的羽毛,和那一声划破长空的啼鸣吧?宋勤孝想了想,说道。
说得好。老秀才点头,换言之,是形与声,是外在的锐利与锋芒。但物极必反,过于锋利,则易折;过于高亢,则易断。一把好刀,若无刀鞘收敛其锋芒,终会伤人伤己。一只好鸡,若只知啼鸣炫耀,不懂蓄力沉潜,也终究难成大器。
而那个疯阿七,他就是你和你儿子的刀鞘!
刀鞘?宋勤孝更糊涂了。
你可知道他属什么?老秀才的眼神变得深邃。
宋勤孝摇了摇头。
老秀才一字一顿地说道:他属牛,丑牛!
牛!
宋勤孝的脑子嗡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他清楚地记得,武侯宅经上说,酉鸡与丑牛,虽是三合,但若不得法,便成斗局,日日纷争,耗损锐气。他之前那个邻居王屠户,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怎么到了疯阿七这里,这属牛的,反倒成了贵邻?
见他满脸困惑,老秀才长叹一声:所以我说,你看人不能只看皮相,看局也不能只看生肖。同是丑牛,那王屠户的势,是向外的争,他的炉火与噪音,是与你家气场的直接冲撞,日日消耗你的心神,此为斗牛,损人不利己。
可疯阿七不同。老秀才指向后院的方向,他的势,是向内的琢!你听到那夜夜不休的笃笃声,以为是疯癫之举。你错了!那是摒弃了世间一切杂念,将所有心神都凝聚于手中刻刀的极致专注!此为神牛,是在用一把刻刀,开垦自己内心的方寸福田!
他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换做旁人,早就倒下了。可他没有,他把所有的痛苦、不甘、疯狂,全都化作了刻刀下的力量。他不是疯了,他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件艺术品,一件在烈火与重锤下,千锤百炼而成的绝世孤品!
酉鸡、巳蛇、丑牛,这才是武侯宅经里真正的三合大局!马寡妇的静,为你家打下根基;你妻子的升,为你家带来希望;而这疯阿七的琢,则是最关键的一步,他用他自己的言传身教,告诉你和你的孩子,如何收敛锋芒,如何沉心静气,如何将一身的才华与锐气,凝聚于一点,雕琢成器!
至此,宋勤孝才算彻彻底底地明白了。
所谓的贵子之局,根本不是什么玄妙的风水阵法,而是一个为人处世,教育子孙的至高道理。
它需要的,是一个安静坚韧的环境(蛇),一个温暖包容的家庭(龙),以及一个能教会孩子专注与沉潜的榜样(牛)。
这三者,缺一不可。
宋勤孝激动得浑身颤抖,他仿佛看到了一条金光大道,在自己和儿子面前缓缓铺开。
他之前所做的一切,歪打正着,竟真的凑齐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贵子之局!
先生我,我该怎么做?他声音发颤地问。
老秀才微微一笑,捋了捋胡须: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善待邻里,心怀感恩,这便是开启局面的钥匙。接下来,你要做的,不是去求,而是去学。
去学马寡妇的静,学你妻子的容,更要去学那疯阿七的琢。而且,不光你要学,更要带着你的儿子,一起去学。
06
从老秀才家出来,宋勤孝走在路上,只觉得脚下轻飘飘的,像是踩在云端。
整个世界,在他的眼中,都变得不一样了。
回到家,看到杨氏正在灯下为文远缝补衣服,那专注温柔的侧脸,在他眼中,仿佛真的化作了一条散发着柔光的祥龙。
他走过去,第一次,笨拙地从身后抱住了妻子。
你你这是干啥?杨氏吓了一跳,脸颊绯红。
没什么,宋勤孝把脸埋在妻子的颈窝,声音闷闷的,就想谢谢你。
谢谢你,做我的妻。
谢谢你,做我家的龙。
第二天,宋勤孝做了一个让杨氏大惊失色的决定。他要带着文远,去拜访后院的疯阿七。
当家的,你疯了?那人那人会伤了孩子的!杨氏拼命阻拦。
宋勤孝却异常坚定,他拉着妻子的手,将老秀才的那番话,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
杨氏听得目瞪口呆,半信半疑,但看到丈夫眼中那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坚定,她最终还是松开了手。
宋勤孝牵着文远,绕到后院那间破败的茅屋前。
笃、笃、笃
那熟悉的雕刻声,此刻听在耳中,不再诡异,反而充满了一种让人心安的韵律。
他深吸一口气,轻轻推开了门。
疯阿七依旧是那个姿势,佝偻着背,对他们的到来,置若罔闻。
宋勤孝也不说话,就那么牵着儿子,静静地站在一旁。
文远起初有些害怕,但很快,他的目光就被疯阿七手中的木头和刻刀吸引了。
他看到,在一片片木屑的飞舞中,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,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慢慢显现出一只鸟儿的轮廓。那专注的神情,那精准的刀法,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。
疯阿七始终没有看他们一眼,仿佛整个世界,只剩下他和他手中的作品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直到天色渐暗,疯阿七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
他拿起那只已经成型的木鸟,吹掉上面的木屑,然后,做了一个让宋勤孝父子都意想不到的动作。
他将那只栩栩如生的木鸟,递到了文远的面前。
文远怯生生地伸出小手,接了过来。
疯阿七那双浑浊却明亮的眼睛,第一次,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孩子,然后沙哑地吐出两个字:拿好。
说完,他便转身,不再理会他们。
宋勤孝知道,这位贵邻,已经用他自己的方式,接纳了他们。
从那天起,每天下午,宋勤孝都会带着文远,去茅屋里待上一个时辰。
他们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。
看疯阿七如何将一块块朽木,化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
文远变了。
他不再只是捧着书本死读,他的眼神里,多了一份沉静与专注。他读书习字,也像疯阿七雕刻一样,一笔一划,都倾注了全部的心神。
他的性子,不再像宋勤孝那般急躁,也不再像之前那般孱弱,而是多了一种如玉石般的温润与坚韧。
转眼,数年过去。
南边钱扒皮的染坊早已臭气熏天,周围的住户苦不堪言。而宋勤孝一家所在的这个小小的院落,却仿佛世外桃源,宁静而祥和。
宋勤孝的金鸡之锐,被妻子的龙之柔情所包容,被马寡妇的蛇之静谧所安抚,更被疯阿七的牛之专注所打磨。
他不再是那个怨天尤人的庄稼汉,脸上多了从容与平和。
而文远,也没有辜负这方水土的滋养。他学问日进,品性敦厚,成了远近闻名的佳子弟。
多年后,宋勤孝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。
他时常会坐在院子里,手里摩挲着那本早已翻烂的武侯宅经。他终于明白,这本书里最大的玄机,不是生肖,不是风水,而是人心。
所谓的贵子之局,不过是爱与尊重的另一种说法。
对伴侣的珍视,是龙凤呈祥的根基;对邻里的友善,是三合之局的开端;而对那些身处困境,却依然坚守内心的疯子的敬意,才是一个家族真正能兴旺发达的密码。
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贵人,有的,只是你是否拥有一双能够发现贵气的眼睛,和一颗懂得珍惜与感恩的心。千金买宅,万金买邻,最终买的,不过是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,和一份让子孙后代足以安身立命的家风。
砖瓦打一个生肖